
董事长随笔
Chairman's Essay
享·童趣
偶见网络上的三张图片:用树叶摆的舞蹈家的图案、一个小男孩套腿儿骑自行车的图片和三个小朋友并排走着的图片。我的脑海中一下子涌出了许多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
记忆中的秋天,小伙伴们用杨树上落下的金黄色叶子的叶柄(我们叫它“根儿”)十字交叉在一起用力往反方向拉,谁手中的根儿没被拉断,谁就赢了。杨树叶的根儿两头粗中间细,中间的颜色如果发黄发白,就不会很结实,一拉就断;而中间发红黑或棕色的根儿,拉的时候更有耐力。为了能在较量中获胜,大家认真地翻捡树叶,挑找又粗又大的根儿。有时为了叫根儿更老、更有劲、更结实一点,会把它放到正穿着布鞋或胶皮鞋的脚底下“闷”着,使其颜色更暗、更有韧劲。大家互相“拉根儿”,有时候是一根决胜负,有时则是“团体赛”,比如各拿出五根或十根,最后剩的多的就是胜利者。胜利了,自然一派喜气洋洋,各自陶醉其中;也有不服输的小伙伴,会要求再来。偶有小伙伴会耍点心眼儿,比如故意将对手的根儿的中心往自己的根头一端交叉,更有甚者,趁人不注意把小手指头混到了根儿下,低着头双手使劲往怀里拉以做掩护。可一旦被发现那就惨了,小伙伴们好几天都不会带他玩了。

为什么我们秋天爱玩“拉根儿”?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许多高大粗壮的杨树,一到秋天,金黄色的落叶就会落满一地。“拉根儿”这个游戏不知道是从哪年哪月兴起的,它承载了我学龄前的许多乐趣,也串起了我许多童年的记忆。十岁之前,我家住在河东区郑庄子棉纺五厂二宿舍九号二楼。棉纺五厂是日本人在1937年建的,解放后被收归国有。工厂正门外有三个宿舍,其中一和三宿舍的房子是普通的联排平房,二宿舍则是原来为厂里高级职员设计建造的日式联排楼房和多排平房。从厂里出来右转即是二宿舍,这里建筑错落有致、环境干净整洁,进门可以看到一个曾经喷过水、养过鱼、开过花的大圆池子,使得整个宿舍在平和中略显讲究。圆池子后面,楼与楼之间留有一小块儿生长着一小群杨树的绿地,在当时我们的眼里,那可是挺大的一片树林。杨树很高、很大,除了粗得抱不过来之外,抬头好像也见不到树梢,被我们小伙伴们奉为玩乐的天堂。我家就住在杨树林的前面,我也常常在里面玩耍沉迷而忘记回家。
童年时没人会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的童年啦”,即使有人讲你也记不住,你也会听不大懂。只有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段时光叫做童年,无论它是否有乐趣、是否幸福和甜蜜,你都不会停止成长。
第二张图片中那个骑自行车的小孩,让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儿时的影子。我小学四年级搬家到河东区向阳楼,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人,十分怀恋过去的小伙伴们。之前,大家无论玩儿还是学习都是相互信任、依赖的,好像谁也离不开谁。学习有学习小组,临近住的三五个同学编在一个小组,一般是谁家的房子大就到谁家去学习,有时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轮换一下。但不管到谁家,同学们都会自觉地学习并在离开前打扫卫生。邻居间也有着浓厚的感情,生活中有许多条线把大家拉近,如我们的家长大多是棉纺厂的同事,我们的哥哥姐姐还是同学,甚至后来结成了夫妻。那时我们邻居间互助、互动,联系频繁,像亲戚一样走动,无须互相防备,也没有过丝毫冲突。现在想来,恍如隔世。
向阳楼离棉五二宿舍应该有七八公里远。由于刚到新的地方,加上与新结识的伙伴玩不到一起,我更加想念二宿舍的小伙伴们。于是,将思念之情化作一股冲动和力量,使用图片中标示的“套腿儿”骑自行车的方式,寻着大人们讲过的陌生的路线,自己愣是“套腿儿”回到了二宿舍!这对我来讲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真正的远行。记得那个夏天,当我来到原住址楼后的一个同学家时,我已大汗淋漓。同学的妈妈出来迎接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她不敢相信我真的是自己从那么老远骑车来的。当时的我,脑袋只比自行车高出一点点,确实很难令人相信我会“套腿儿”骑车而来。记得我跟小朋友们玩儿了会儿后,心里踏实了,就又骑车回家了。我妈妈说找了我半天不知道我去哪玩了,根本就不信我能骑车骑得那么远。多少年以后,我和小学同学们在一起聚会时才知道,我的两个同学在我骑车回棉五后不久,也骑车到向阳楼找过我一次,只是很遗憾没有找到,他们以为向阳楼也像二宿舍那么小,一找一问肯定就能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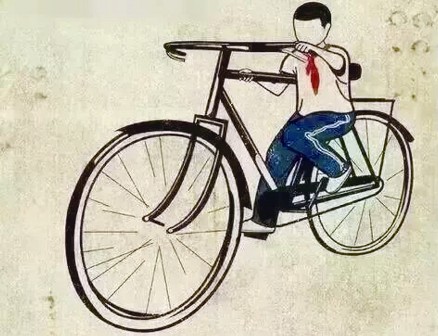
童年如梦,岁月如花。曾经玩耍的情景好像还不停地在眼前晃动。那时的游戏,武的有打尕儿、撞拐、弹玻璃球、骑马砸骆驼、推轱辘圈儿等,文的有看万花筒、存糖纸、跳绳、跳房子、纸三角、拔根儿、集商标、小人书、娱乐琴、望远镜等等。于当时的我们而言,那都是好玩的项目。那时小伙伴们一起玩,家长都非常放心,没有人管,更没有人为维护自己的孩子而吓唬或打别人的孩子,包括对男孩子有时自己用“家伙”做玩具的行为,也基本上持放纵态度。我们会到附近叫做“大东坑”的河边捡粗铁丝做成推铁环的推把及铁环;还会把方块木头削尖成圆锥体后,用铁榔头在顶尖的地方再砸上一个自行车废轴承中的钢制滚珠制成精致的尕儿。反观现在,我认为一些家长对孩子炫耀性的疼、养、玩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博取声誉的象征罢了。
二宿舍的住户有工程师、老职员、医生、技术工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干部,但无论谁家,像样的玩具都很少。即便如此,家长们也没有秘而不宣的,哪家都不吝与其他小朋友分享有限的资源。记得有个邻居家的女孩儿有许多糖纸,她特别精心地夹在了书本中。这个秘密不知道叫谁发现了,于是大家就起哄似的要求看看,于是她妈妈就让她拿给想看的小朋友,当然了要洗干净手。之后邻家的女孩儿就耐心地给我们翻看她收集的天津的、上海的、北京的和许多外地的纸糖纸和玻璃糖纸。那些糖纸都很漂亮,色彩斑斓、美妙而富有幻想。尤其是玻璃糖纸,从书本里拿出来放到热乎乎的手心后,平整的糖纸会慢慢地翘起来、动起来,于是我们就又多了一点“学问”,知道糖纸有“活的”了。
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和小伙伴们还唱过的童谣:“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点点点,点牛眼,牛眼花,七个碟子八个花,吃不了剩给谁?剩给他。”
“一网不逮鱼啊,两网去赶集呀,三网逮个大金鱼呀。”……这些可能都是跟着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玩时唱的。记不清是什么场景了,但是能很清楚地唱出来。

童年少烦恼,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失落、迷茫和无奈,没有少年时代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安与焦躁,更没有因为胆怯而显现出矫揉造作的空虚和对大人们管教的怒气。想起来,那时很单调,很单纯,但玩的很有趣。
长大至今,总是忘不了儿时的驻地,常是不自觉地向着城市的东方瞭望。其实除了眼前的高楼大厦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只是有一种感觉,好像望着那个方向就能看到了儿时的情景和儿时的玩伴。童年的美好,不会因为人们的留恋而停滞不前,我们对理想的向往和苦恋,也大多数来自童年时种下的种子。
最初我们怀揣着一颗清纯的心张望世界,历经世事,方觉曾经珍贵。而人生本来就是直播,没有暂停,也不能重来,正因如此,懂得欣赏每一段风景才最为重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从童心中来,“我信你就不会走,你走,我就当你没来过”,将未泯稚气深埋心底的某个角落。
如今,我的生活早已按部就班,儿时的伙伴们也更是强者自救,圣者渡人,万般心胸,成就幸福。偶尔小聚,我们都会真心实意地聊起童年趣事,不会像有些事业有成之人那样,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为了粉饰过去而昧着良心自欺欺人。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童年的真实中才能寻找到真正的乐趣。
